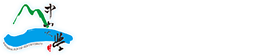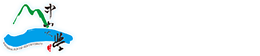「中間選民」是啥玩意兒?(經濟日報)
作者:中山大學政經系助理教授劉孟奇
這次總統大選,媒體經常出現「中間選民」這個名詞,而且中間選民的意向,似乎被視為會對於選舉結果產生舉足輕重的影響。到底誰是中間選民?這其實不是一個容易回答的問題。不過應該可以說,目前社會對於中間選民的一般印象就是:不特別偏向某一個政黨或政治立場。或者說,「保持中立」的選民,就是中間選民。
為什麼在選舉當中,很多人或媒體喜歡宣稱自己代表中間選民?我的觀察是,宣稱自己代表中間選民,好像可以讓自己的發言更具份量。特別是當媒體提到中間選民的時候,總會出現一些似乎具有高度道德性與理想性的詞彙。
這些說法其實有一些值得商榷之處。首先,不表態的選民不見得就是所謂的中間選民,而可能是不關心政治結果的選民。其次,如果中間選民的性格就是所謂的「不偏不倚、客觀理性」,那麼,他們對於政治、社會的發展方向與結果,恐怕就沒有什麼影響力。
為什麼?因為所謂的「不偏不倚」,很容易被簡化為「各打五十大板」。不管候選人如何試圖在邊際上調整政策,爭取更多的支持,都會被堅持不表態、難以取悅的「中間選民代言人」以負面的方式檢視,吹毛求疵地加以批評。候選人很快就會發現,調整政策討好這些中間選民代言人的邊際效果接近零。既然如此,還不如針對立場鮮明的選民,提出能明確打動他們的主張。這就是越到選舉後期,這些中間選民代言人就會越被邊緣化的主要原因。
除此之外,所謂的「客觀理性」常被詮釋為「沒有預設立場」,這與經濟學上的「理性」定義很不一樣,後者所指的是「在選擇上具有一致性、不會顛三倒四」。
人必須具有明確的價值觀,才能做出前後一致的選擇。一群選民的選擇如果沒有一致性,自相矛盾,讓候選人無從遵循,就難以對政策有實質影響。如果選民不想做出有一致性的取捨———既要對社會福利大幅加碼,又要財政收支四年平衡;既要課富人稅、取消租稅優惠,又要吸引投資、創造就業;既不增稅,又不舉債,又要大幅增加公共建設;既要人人有大學念,又要80%的學生念國立大學———那麼候選人自然只有大開芭樂票,到頭來,中間選民自詡的「客觀理性」,換來的將只是一堆既不合理,又無法實現的空洞承諾。
在歐美的政治脈絡當中,所謂的中間選民,並不是指沒有立場的假中立、沒有價值觀的虛無,而是指:如果我們讓一位中間選民對一群政策選項進行選擇的話,整體看來,她(他)的選擇比較不會明顯地偏左或偏右、偏自由派或偏保守派。
舉例來說,在經濟政策上,一般以「左」與「右」來劃分政策的兩極。我們可以問一個選民,他是否支持下列幾個關於政策的陳述:「面對外國產品的競爭,政府應該補貼廠商,或實施貿易保護,以保護國內就業」、「大學應該以低學費的公立大學為主」、「政府應該實施最低工資」、「政府應該保障弱勢族群的就業機會」。一個明顯偏左的選民,可能會對上述四個陳述都投下贊成票;一個明顯偏右的選民,可能會對上述四個陳述都投下反對票;一個中間選民,就可能不贊成前兩個陳述,而贊成後兩個陳述。而一個人如果對四項陳述都沒有立場,那叫做「沒有意見」,不叫做中間選民。
在社會政策上,一般以「自由」與「保守」來劃分政策的兩極。我們可以問一個選民,他是否支持下列幾個陳述:「人民可以焚燒國旗」、「公立學校不宜開設宗教課程」、「大麻可以合法化」、「可以研發複製人技術」。一個明顯偏自由派的選民,可能會對上述四個陳述都投下贊成票;一個明顯偏保守派的選民,可能會對上述四個陳述都投下反對票;一個中間選民,可能支持前兩項陳述而反對後兩項陳述。同樣地,我們不應把「沒有意見」當成是中間選民。
公共政策不是在一個真空的烏托邦中進行,而是在一個充滿利益團體的現實中,設法讓法規制度與資源分配的天平不朝一端過度傾斜。我們與其不切實際地期待一群高高在上的中間選民替社會決定未來,還不如務實地重視這些利益團體是否擁有對稱的資源與力量,是否會被不實的資訊所蒙蔽,是否能在公平的制度下進行競爭。
歸根究抵,我們不如承認,人不可能沒有立場而能認識世界,也不可能沒有價值觀,而能在一個時時需要進行抉擇的世界中安身立命。價值虛無不能成為道德優位的背書,虛假的中立也不能成為批判的安全避風港。從另一方面來說,當我們承認我們的批判是有立場的,這代表我們承認自己犯錯的可能,也提供了妥協調和的空間;當我們承認我們的選擇是有價值觀的,這代表我們知道選擇的代價,也才能讓選擇擁有不可或缺的意義與重量。
2004-03-28╱經濟日報╱第24版╱知識經濟╱劉孟奇
這次總統大選,媒體經常出現「中間選民」這個名詞,而且中間選民的意向,似乎被視為會對於選舉結果產生舉足輕重的影響。到底誰是中間選民?這其實不是一個容易回答的問題。不過應該可以說,目前社會對於中間選民的一般印象就是:不特別偏向某一個政黨或政治立場。或者說,「保持中立」的選民,就是中間選民。
為什麼在選舉當中,很多人或媒體喜歡宣稱自己代表中間選民?我的觀察是,宣稱自己代表中間選民,好像可以讓自己的發言更具份量。特別是當媒體提到中間選民的時候,總會出現一些似乎具有高度道德性與理想性的詞彙。
這些說法其實有一些值得商榷之處。首先,不表態的選民不見得就是所謂的中間選民,而可能是不關心政治結果的選民。其次,如果中間選民的性格就是所謂的「不偏不倚、客觀理性」,那麼,他們對於政治、社會的發展方向與結果,恐怕就沒有什麼影響力。
為什麼?因為所謂的「不偏不倚」,很容易被簡化為「各打五十大板」。不管候選人如何試圖在邊際上調整政策,爭取更多的支持,都會被堅持不表態、難以取悅的「中間選民代言人」以負面的方式檢視,吹毛求疵地加以批評。候選人很快就會發現,調整政策討好這些中間選民代言人的邊際效果接近零。既然如此,還不如針對立場鮮明的選民,提出能明確打動他們的主張。這就是越到選舉後期,這些中間選民代言人就會越被邊緣化的主要原因。
除此之外,所謂的「客觀理性」常被詮釋為「沒有預設立場」,這與經濟學上的「理性」定義很不一樣,後者所指的是「在選擇上具有一致性、不會顛三倒四」。
人必須具有明確的價值觀,才能做出前後一致的選擇。一群選民的選擇如果沒有一致性,自相矛盾,讓候選人無從遵循,就難以對政策有實質影響。如果選民不想做出有一致性的取捨———既要對社會福利大幅加碼,又要財政收支四年平衡;既要課富人稅、取消租稅優惠,又要吸引投資、創造就業;既不增稅,又不舉債,又要大幅增加公共建設;既要人人有大學念,又要80%的學生念國立大學———那麼候選人自然只有大開芭樂票,到頭來,中間選民自詡的「客觀理性」,換來的將只是一堆既不合理,又無法實現的空洞承諾。
在歐美的政治脈絡當中,所謂的中間選民,並不是指沒有立場的假中立、沒有價值觀的虛無,而是指:如果我們讓一位中間選民對一群政策選項進行選擇的話,整體看來,她(他)的選擇比較不會明顯地偏左或偏右、偏自由派或偏保守派。
舉例來說,在經濟政策上,一般以「左」與「右」來劃分政策的兩極。我們可以問一個選民,他是否支持下列幾個關於政策的陳述:「面對外國產品的競爭,政府應該補貼廠商,或實施貿易保護,以保護國內就業」、「大學應該以低學費的公立大學為主」、「政府應該實施最低工資」、「政府應該保障弱勢族群的就業機會」。一個明顯偏左的選民,可能會對上述四個陳述都投下贊成票;一個明顯偏右的選民,可能會對上述四個陳述都投下反對票;一個中間選民,就可能不贊成前兩個陳述,而贊成後兩個陳述。而一個人如果對四項陳述都沒有立場,那叫做「沒有意見」,不叫做中間選民。
在社會政策上,一般以「自由」與「保守」來劃分政策的兩極。我們可以問一個選民,他是否支持下列幾個陳述:「人民可以焚燒國旗」、「公立學校不宜開設宗教課程」、「大麻可以合法化」、「可以研發複製人技術」。一個明顯偏自由派的選民,可能會對上述四個陳述都投下贊成票;一個明顯偏保守派的選民,可能會對上述四個陳述都投下反對票;一個中間選民,可能支持前兩項陳述而反對後兩項陳述。同樣地,我們不應把「沒有意見」當成是中間選民。
公共政策不是在一個真空的烏托邦中進行,而是在一個充滿利益團體的現實中,設法讓法規制度與資源分配的天平不朝一端過度傾斜。我們與其不切實際地期待一群高高在上的中間選民替社會決定未來,還不如務實地重視這些利益團體是否擁有對稱的資源與力量,是否會被不實的資訊所蒙蔽,是否能在公平的制度下進行競爭。
歸根究抵,我們不如承認,人不可能沒有立場而能認識世界,也不可能沒有價值觀,而能在一個時時需要進行抉擇的世界中安身立命。價值虛無不能成為道德優位的背書,虛假的中立也不能成為批判的安全避風港。從另一方面來說,當我們承認我們的批判是有立場的,這代表我們承認自己犯錯的可能,也提供了妥協調和的空間;當我們承認我們的選擇是有價值觀的,這代表我們知道選擇的代價,也才能讓選擇擁有不可或缺的意義與重量。
2004-03-28╱經濟日報╱第24版╱知識經濟╱劉孟奇
瀏覽數:
分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