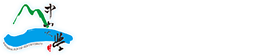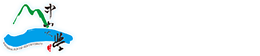哨船頭小記(中國時報)
我們可以一八六四年史溫侯剛在打狗港一艘廢船三葉號上任職副領事辦公的眼光看待哨船頭的小漁港,就把福德宮這間小土地公廟擺進去吧!
清晨六點、住在哈瑪星的人們如果早起的話,一定會聽到從海岸的方向傳來晨鐘的聲音,但那鐘聲似乎又遠遠高掛在山上;剛搬來哈瑪星時,在睡夢中常常被這鐘聲吵醒,一直想循聲去尋找那鐘聲的來源處;在哈瑪星住久了,約略可以判斷這鐘聲可能來自海岸邊的哨船頭山,那?的山頭上,除了二級古蹟英國領事館外,還有一座十八王公廟,山下的安海街三十二巷內,有一間據說是西元一五五一年建廟的開台福德宮,這是一間小小的土地公廟,幾乎和其他民宅混居一起,分不清彼此了!
安海街、安船街、哨船街都是哨船頭山東側這一帶的古老巷弄,歷史的感覺特別厚重,但它依然還是人們生活的地方,有一處位在巷弄深處的小吃攤,從清晨賣到中午,由於一碗魚湯只賣三十元,一碗乾麵二十元,新鮮味美,食客川流不息,還吸引了大批老遠專程來吃的計程車司機和登山客、海泳客,由於地處偏遠,巷弄寧靜無人,隨處好停車,附近又有海港的景色,吃頓飯是很舒服的,觀光客都只在外頭的大馬路上呼嘯而過,要發現巷弄中的世界不容易。
史溫侯
站在福德宮前的小廟埕,抬頭可以望見英國領事館美麗的洋樓建築彷彿遺世獨立,睥睨著山下的大港;我讀過史料才知道,替打狗山的台灣獼猴鑑定為台灣特有種的史溫侯,在台灣的博物學界貢獻輝煌的史溫侯,例如斯文豪氏攀木蜥蜴,以另一個譯名「斯文豪」為之命名的史溫侯,曾經是一八六一年第一位英國來台外交官的史溫侯,經常於工作之餘行走台灣各地調查生態的史溫侯,其實並沒有住過哨船頭山上的這間美麗洋樓,他在一八六五年擔任英國領事館領事一職,和福德宮旁的居民一樣,住在哨船頭山東側的山下民宅中辦公,一八六七年英國領事館遷至哨船頭山上的天利行洋樓,雖然是史溫侯一手推動的,可是他在一八六六年便奉調廈門,無緣進駐這棟紅磚樓。
沿著安海街三十二巷福德宮旁的狹窄巷弄,找到一條山坡小徑,可以一路爬升至山頂上,那條山坡小徑旁,原本可以看見一塊「台灣關地界碑」,原是清代打狗稅關的文物,最近剛被高雄市歷史博物館收去典藏,避免風吹日曬磨損了石碑;打狗稅關現址為水產試驗所宿舍,也是一棟古蹟,就在英國領事館下方的哨船街七號,那兒也立有一塊「台灣關地界碑」,還有一塊在領事館北側的山坡出土,民國八十五年被送到台北海關博物館保存,福德宮這一塊是民國八十七年二月,準備慶祝土地公生日,進行巷道拓寬工程,開挖地基時發現的;山頂上原本是英國領事館的基地和墓園,後來加入的十八王公廟早年原本蓋在中山大學某一處校園內,因為中山大學的建校,市政府只好以地易地,同意將之遷到英國領事館的隔壁。
洋鬼鬧事
然而這之間發生一件有趣的歷史傳聞,雖然市政府同意了十八王公廟遷移至英領館旁,可是原來的居民是住在英領館旁墓園?的洋將軍鬼卻不同意,事情鬧了一陣子,聽說山頭上的老榕樹一夜之間都枯黃了!乩童求問的結果,最後只好又為洋將軍的鬼魂蓋了廟才平息,據說乩童看見的洋將軍鬼有二位,那就是為什麼十八王公廟的旁邊,又多了一間小廟叫二位元帥廟。
後來我養成了早起健行的習慣,壽山有許多條錯綜複雜適合健行的林中小徑,其中一條較不為人所知,就是從安海街三十二巷上山,從英國領事館的山頭,沿著藏隱在半山腰中的步道走,走完南壽山的支脈哨船頭山,還可以穿過中山大學校園,一直走到文學院後方去爬少女峰呢!清晨六點不到,當我到達安海街福德宮旁的巷子想要往上爬升時,往往遇見福德宮剛開廟門,而且常常有趕早來拜拜搶得頭籌的老婦人正要插第一炷香。
從來不知道廟門在清晨六點就開了!也不知道這麼早就有老婦人拎著水果來拜拜,一早便坐在廟埕前的老阿媽總是說這間廟四百五十冬啊!那清晨的寧靜氛圍正是適合向神,向內心祈禱的好時光,開廟門的第一位祈求者,我想任誰皆會特別傾聽注意吧!何況是仁慈的土地公呢!六點準時的晨鐘來自山上的十八王公廟,那時的我正站在廟旁的山背上迎接從大武山方向升起的朝陽,大武山就在高雄港的東方,天氣晴朗的時候,從壽山上看得見大武山浮現在雲霧之上,太陽之下,早起的登山客如果運氣好的話,可以從英國領事館這個角度,望見高雄港灣上剛升起的火紅太陽和大武山以及東帝士八十五層摩天樓和雲霧互相輝映的奇景。
大武山地標
文獻上記載,除了從壽山看得見大武山外,早期從大陸沿海航行至打狗港的漁民,往往以大武山為標的,快接近打狗外海時,只要看見遠方海面的天空中,大武山浮現在雲霧之上,便知道打狗港快要到了!同樣的大武山,不同的時代,史溫侯應該也在打狗山頭上凝望過吧!
與大武山在僻靜的清晨山頭上初次相遇的經驗是很像宗教體驗的,那時的山下大多數的人們還沉睡著,我已經一連十數天每天清晨都維持在六點上山,我很喜歡這種清晨既清醒的清新感覺,但我早忘了文獻上的記載,從來沒想到這個角度看得到大武山,高雄空氣的污濁是常態,遠方的天空總是灰濛濛的望不遠,有一天清晨出門並未特別去留意天氣,剛剛爬上山喘個氣轉個身,嶙峋的南北大武山頭就像諸神羅列般忽然地浮現在雲霧之上,強烈地撞擊著措手不及的我,讓我讚嘆不已;我記得那天雲特別地白,遠方雲端之上的天空出奇地藍,是個適合出遊的日子,住在雲霧之中的諸神想必也迫不及待地出來遊玩而讓我窺見吧!
清晨凝視朝陽的儀式結束之後,我才鑽進仍然幽森暗黑的森林開始林中小徑的健行,我知道我站立和走過的地方曾經是埋藏異鄉人的墓園,這群遠離家鄉在哨船頭山上安息的魂魄,曾經凝望過大武山嗎?然而我一點也不感到害怕,反而清楚意識到這些在地歷史很少人知道,走這條幽隱小徑的人也不多,才讓我有機會獨自避靜在山頭上,不被打擾,迎接著難以形容的高雄美景。
建廟年代爭議
覺得很奇怪,高雄市政府關於哈瑪星的古蹟導覽有大清時代的英國領事館、水產試驗所(前清稅關)、日據時代的打狗驛、打狗第一小學、武德殿、愛國婦人會館、山形屋出版社等等,卻獨缺這座西元一五五一年建廟的福德宮,以歷史年代來說,這間土地公廟可要比上述的古蹟都要悠久,後來我才知道,高雄市的歷史學者對於福德宮自稱的建廟年代一直有爭議,而把它遺忘在山腳下的民宅巷弄中。
歷史學者在文獻上不敢茍同小土地公廟自稱的建廟年代,可是我們也能猜測到,十六世紀最早來到打狗港的漁夫或海盜們所建的土地公小廟,哪能想到往後未來的歷史層面而用文字加以記錄廟的歷史呢?
位於高雄港北岸的哨船頭是打狗最早的漁民聚落之一,「哨船」為古時候的巡邏船或監視船,因為清代派駐兵船在此駐哨,故稱此地為哨船頭,西元一八五八年列強與清廷簽訂「天津條約」,要求開放台灣為通商口岸之一,並在一八六三年增開打狗為安平的外口港,於是打狗港從一個小漁港躍升為國際貿易商港,外國官員、商人、傳教士接踵而至。
成為國際商港的打狗港,在港口南北兩側代表的是不同的貿易文化與型態,南岸的旗津以漢人的生活型態為主,北岸的哨船頭則多洋行、商行、海關、領事館;日治時期,哨船頭成為日籍漁民住宅宿舍群集之處,儼然是個國際村。
被遺忘的庶民史
我可以想見,打狗港的哨船頭在成為國際商港之前的小漁港時期的歷史是被遺忘的,福德宮的存在也許可以代表這個時期的庶民史。
歷史往往是用當代的眼光去看的,漁人碼頭旁被遺忘的福德宮,也許提醒著我們,高雄港開埠已屆一百四十年,那麼一百四十年前呢?
我們可以一八六四年史溫侯剛在打狗港一艘廢船三葉號上任職副領事辦公的眼光看待哨船頭的小漁港,就把福德宮這間小土地公廟擺進去吧!那時還沒有日本人大規模的填海造陸以及開挖第一船渠,所以並沒有現代的漁人碼頭,環境背景和現在是不太一樣的,我寧可承認土地公廟的存在穿越整個打狗港歷史,文獻上記載著一八六五年打狗的副領事館升格為領事館並遷至哨船頭山東側的民宅,也許就在福德宮附近也說不定,一個進入漢人聚落的西方外交官和博物學家遇見了當地一間小土地公廟也是可以被想像的,只是歷史記載不及而已。
關於土地公廟的庶民史因為歷史記載不詳而被忽略,遠不如一位在地的老阿媽的單純信仰「這間廟四百五十冬啊!」
(王家祥,曾任副刊主編七年,業餘擔任過高雄柴山自然公園促進會會長。曾獲時報文學獎、聯合報文學獎、賴和文學獎等獎項,散文作品多次入選年度散文選,其中「遇見一棵樹」曾被編入國中國文教材。)
2004-04-26╱中國時報╱第E7版╱人間副刊╱王家祥
清晨六點、住在哈瑪星的人們如果早起的話,一定會聽到從海岸的方向傳來晨鐘的聲音,但那鐘聲似乎又遠遠高掛在山上;剛搬來哈瑪星時,在睡夢中常常被這鐘聲吵醒,一直想循聲去尋找那鐘聲的來源處;在哈瑪星住久了,約略可以判斷這鐘聲可能來自海岸邊的哨船頭山,那?的山頭上,除了二級古蹟英國領事館外,還有一座十八王公廟,山下的安海街三十二巷內,有一間據說是西元一五五一年建廟的開台福德宮,這是一間小小的土地公廟,幾乎和其他民宅混居一起,分不清彼此了!
安海街、安船街、哨船街都是哨船頭山東側這一帶的古老巷弄,歷史的感覺特別厚重,但它依然還是人們生活的地方,有一處位在巷弄深處的小吃攤,從清晨賣到中午,由於一碗魚湯只賣三十元,一碗乾麵二十元,新鮮味美,食客川流不息,還吸引了大批老遠專程來吃的計程車司機和登山客、海泳客,由於地處偏遠,巷弄寧靜無人,隨處好停車,附近又有海港的景色,吃頓飯是很舒服的,觀光客都只在外頭的大馬路上呼嘯而過,要發現巷弄中的世界不容易。
史溫侯
站在福德宮前的小廟埕,抬頭可以望見英國領事館美麗的洋樓建築彷彿遺世獨立,睥睨著山下的大港;我讀過史料才知道,替打狗山的台灣獼猴鑑定為台灣特有種的史溫侯,在台灣的博物學界貢獻輝煌的史溫侯,例如斯文豪氏攀木蜥蜴,以另一個譯名「斯文豪」為之命名的史溫侯,曾經是一八六一年第一位英國來台外交官的史溫侯,經常於工作之餘行走台灣各地調查生態的史溫侯,其實並沒有住過哨船頭山上的這間美麗洋樓,他在一八六五年擔任英國領事館領事一職,和福德宮旁的居民一樣,住在哨船頭山東側的山下民宅中辦公,一八六七年英國領事館遷至哨船頭山上的天利行洋樓,雖然是史溫侯一手推動的,可是他在一八六六年便奉調廈門,無緣進駐這棟紅磚樓。
沿著安海街三十二巷福德宮旁的狹窄巷弄,找到一條山坡小徑,可以一路爬升至山頂上,那條山坡小徑旁,原本可以看見一塊「台灣關地界碑」,原是清代打狗稅關的文物,最近剛被高雄市歷史博物館收去典藏,避免風吹日曬磨損了石碑;打狗稅關現址為水產試驗所宿舍,也是一棟古蹟,就在英國領事館下方的哨船街七號,那兒也立有一塊「台灣關地界碑」,還有一塊在領事館北側的山坡出土,民國八十五年被送到台北海關博物館保存,福德宮這一塊是民國八十七年二月,準備慶祝土地公生日,進行巷道拓寬工程,開挖地基時發現的;山頂上原本是英國領事館的基地和墓園,後來加入的十八王公廟早年原本蓋在中山大學某一處校園內,因為中山大學的建校,市政府只好以地易地,同意將之遷到英國領事館的隔壁。
洋鬼鬧事
然而這之間發生一件有趣的歷史傳聞,雖然市政府同意了十八王公廟遷移至英領館旁,可是原來的居民是住在英領館旁墓園?的洋將軍鬼卻不同意,事情鬧了一陣子,聽說山頭上的老榕樹一夜之間都枯黃了!乩童求問的結果,最後只好又為洋將軍的鬼魂蓋了廟才平息,據說乩童看見的洋將軍鬼有二位,那就是為什麼十八王公廟的旁邊,又多了一間小廟叫二位元帥廟。
後來我養成了早起健行的習慣,壽山有許多條錯綜複雜適合健行的林中小徑,其中一條較不為人所知,就是從安海街三十二巷上山,從英國領事館的山頭,沿著藏隱在半山腰中的步道走,走完南壽山的支脈哨船頭山,還可以穿過中山大學校園,一直走到文學院後方去爬少女峰呢!清晨六點不到,當我到達安海街福德宮旁的巷子想要往上爬升時,往往遇見福德宮剛開廟門,而且常常有趕早來拜拜搶得頭籌的老婦人正要插第一炷香。
從來不知道廟門在清晨六點就開了!也不知道這麼早就有老婦人拎著水果來拜拜,一早便坐在廟埕前的老阿媽總是說這間廟四百五十冬啊!那清晨的寧靜氛圍正是適合向神,向內心祈禱的好時光,開廟門的第一位祈求者,我想任誰皆會特別傾聽注意吧!何況是仁慈的土地公呢!六點準時的晨鐘來自山上的十八王公廟,那時的我正站在廟旁的山背上迎接從大武山方向升起的朝陽,大武山就在高雄港的東方,天氣晴朗的時候,從壽山上看得見大武山浮現在雲霧之上,太陽之下,早起的登山客如果運氣好的話,可以從英國領事館這個角度,望見高雄港灣上剛升起的火紅太陽和大武山以及東帝士八十五層摩天樓和雲霧互相輝映的奇景。
大武山地標
文獻上記載,除了從壽山看得見大武山外,早期從大陸沿海航行至打狗港的漁民,往往以大武山為標的,快接近打狗外海時,只要看見遠方海面的天空中,大武山浮現在雲霧之上,便知道打狗港快要到了!同樣的大武山,不同的時代,史溫侯應該也在打狗山頭上凝望過吧!
與大武山在僻靜的清晨山頭上初次相遇的經驗是很像宗教體驗的,那時的山下大多數的人們還沉睡著,我已經一連十數天每天清晨都維持在六點上山,我很喜歡這種清晨既清醒的清新感覺,但我早忘了文獻上的記載,從來沒想到這個角度看得到大武山,高雄空氣的污濁是常態,遠方的天空總是灰濛濛的望不遠,有一天清晨出門並未特別去留意天氣,剛剛爬上山喘個氣轉個身,嶙峋的南北大武山頭就像諸神羅列般忽然地浮現在雲霧之上,強烈地撞擊著措手不及的我,讓我讚嘆不已;我記得那天雲特別地白,遠方雲端之上的天空出奇地藍,是個適合出遊的日子,住在雲霧之中的諸神想必也迫不及待地出來遊玩而讓我窺見吧!
清晨凝視朝陽的儀式結束之後,我才鑽進仍然幽森暗黑的森林開始林中小徑的健行,我知道我站立和走過的地方曾經是埋藏異鄉人的墓園,這群遠離家鄉在哨船頭山上安息的魂魄,曾經凝望過大武山嗎?然而我一點也不感到害怕,反而清楚意識到這些在地歷史很少人知道,走這條幽隱小徑的人也不多,才讓我有機會獨自避靜在山頭上,不被打擾,迎接著難以形容的高雄美景。
建廟年代爭議
覺得很奇怪,高雄市政府關於哈瑪星的古蹟導覽有大清時代的英國領事館、水產試驗所(前清稅關)、日據時代的打狗驛、打狗第一小學、武德殿、愛國婦人會館、山形屋出版社等等,卻獨缺這座西元一五五一年建廟的福德宮,以歷史年代來說,這間土地公廟可要比上述的古蹟都要悠久,後來我才知道,高雄市的歷史學者對於福德宮自稱的建廟年代一直有爭議,而把它遺忘在山腳下的民宅巷弄中。
歷史學者在文獻上不敢茍同小土地公廟自稱的建廟年代,可是我們也能猜測到,十六世紀最早來到打狗港的漁夫或海盜們所建的土地公小廟,哪能想到往後未來的歷史層面而用文字加以記錄廟的歷史呢?
位於高雄港北岸的哨船頭是打狗最早的漁民聚落之一,「哨船」為古時候的巡邏船或監視船,因為清代派駐兵船在此駐哨,故稱此地為哨船頭,西元一八五八年列強與清廷簽訂「天津條約」,要求開放台灣為通商口岸之一,並在一八六三年增開打狗為安平的外口港,於是打狗港從一個小漁港躍升為國際貿易商港,外國官員、商人、傳教士接踵而至。
成為國際商港的打狗港,在港口南北兩側代表的是不同的貿易文化與型態,南岸的旗津以漢人的生活型態為主,北岸的哨船頭則多洋行、商行、海關、領事館;日治時期,哨船頭成為日籍漁民住宅宿舍群集之處,儼然是個國際村。
被遺忘的庶民史
我可以想見,打狗港的哨船頭在成為國際商港之前的小漁港時期的歷史是被遺忘的,福德宮的存在也許可以代表這個時期的庶民史。
歷史往往是用當代的眼光去看的,漁人碼頭旁被遺忘的福德宮,也許提醒著我們,高雄港開埠已屆一百四十年,那麼一百四十年前呢?
我們可以一八六四年史溫侯剛在打狗港一艘廢船三葉號上任職副領事辦公的眼光看待哨船頭的小漁港,就把福德宮這間小土地公廟擺進去吧!那時還沒有日本人大規模的填海造陸以及開挖第一船渠,所以並沒有現代的漁人碼頭,環境背景和現在是不太一樣的,我寧可承認土地公廟的存在穿越整個打狗港歷史,文獻上記載著一八六五年打狗的副領事館升格為領事館並遷至哨船頭山東側的民宅,也許就在福德宮附近也說不定,一個進入漢人聚落的西方外交官和博物學家遇見了當地一間小土地公廟也是可以被想像的,只是歷史記載不及而已。
關於土地公廟的庶民史因為歷史記載不詳而被忽略,遠不如一位在地的老阿媽的單純信仰「這間廟四百五十冬啊!」
(王家祥,曾任副刊主編七年,業餘擔任過高雄柴山自然公園促進會會長。曾獲時報文學獎、聯合報文學獎、賴和文學獎等獎項,散文作品多次入選年度散文選,其中「遇見一棵樹」曾被編入國中國文教材。)
2004-04-26╱中國時報╱第E7版╱人間副刊╱王家祥
瀏覽數:
分享